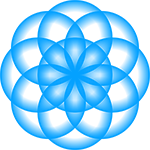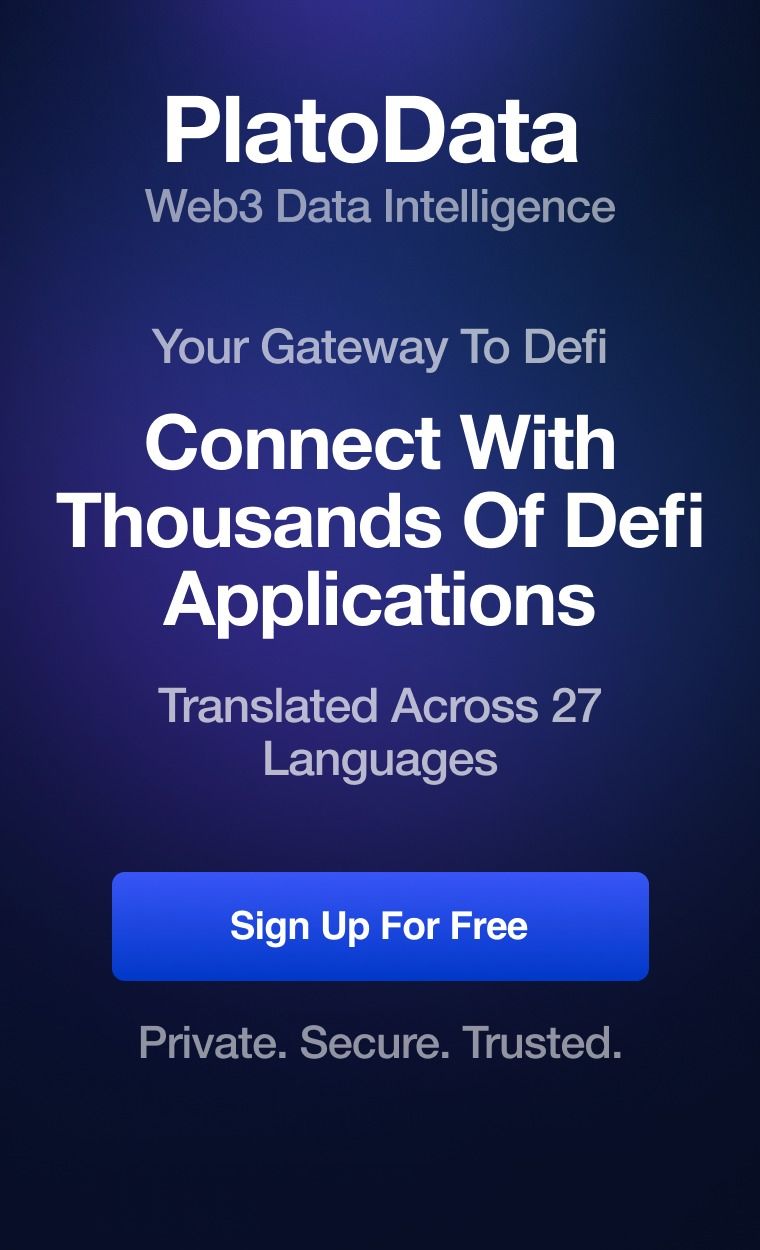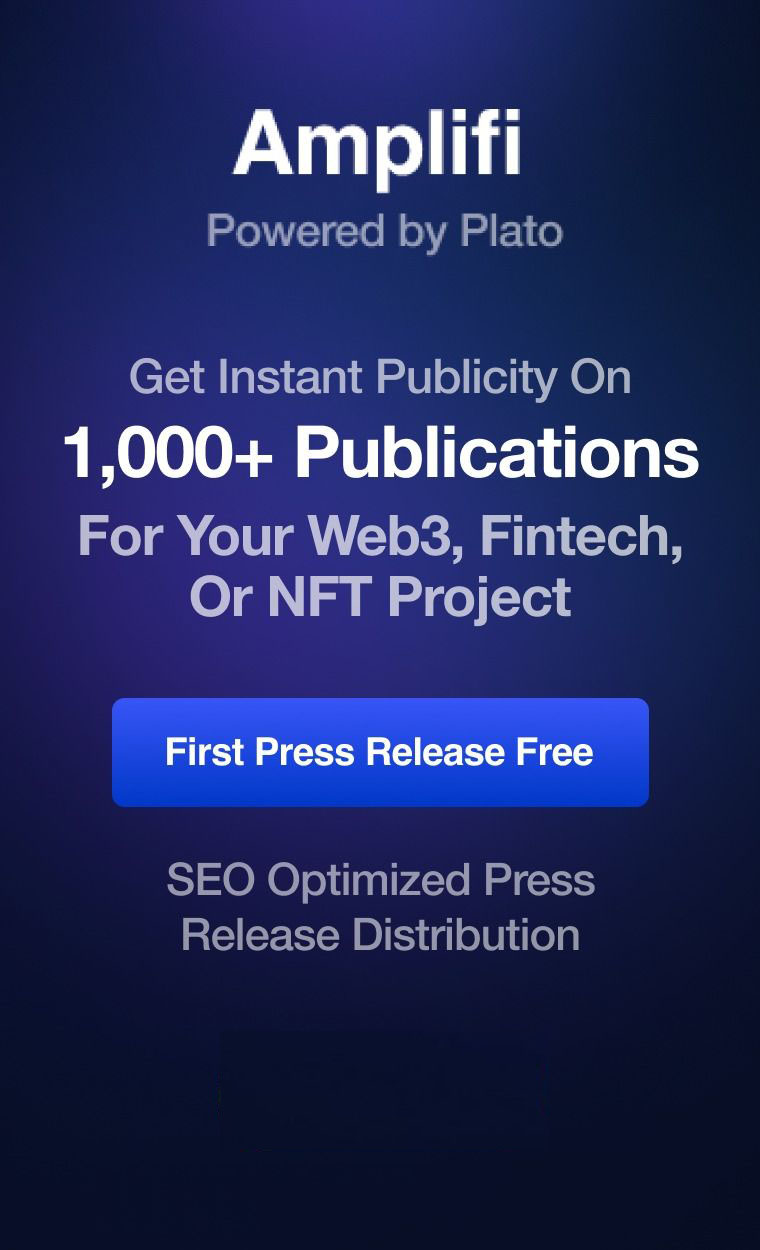介绍
伊什梅尔·阿卜杜斯·萨布尔 (Ishmail Abdus-Saboor) 从小在费城长大,从小就对自然世界的多样性着迷。在三年级老师摩尔先生的指导下,他在大自然中漫步,这让他着迷。 “我们必须与野生动物互动和接触,并在它们的原生环境中观察动物,”他回忆道。阿卜杜勒-萨布尔还把猫、狗、蜥蜴、蛇和海龟等各种动物带进了他的三层楼家里,并攒了零用钱买了一本教他有关海龟的杂志。当大人问他长大后想做什么时,“我说我想成为一名科学家,”他说。 “我总是扬起眉毛。”
阿卜杜勒-萨布尔并没有偏离这个目标。今天,他是一个 生物科学副教授 在哥伦比亚大学 Mortimer B. Zuckerman 心脑行为研究所学习 大脑如何决定 触摸皮肤是痛苦的还是愉快的。 “尽管这个问题对于人类经验来说至关重要,但用令人满意的分子细节来解释仍然令人困惑,”他说。由于皮肤是我们最大的感觉器官,也是通向环境的主要通道,因此它可能为治疗从慢性疼痛到抑郁等疾病提供线索。
为了找到这些线索,阿卜杜斯-萨布尔沿着皮肤到大脑轴探测了神经系统的每个接合点。他不像许多其他人那样只关注皮肤或只关注大脑。 “我们将这两个世界融合在一起,”他说。他补充说,这种方法需要掌握两套技术、阅读两套文献并参加两套科学会议。 “它为我们提供了独特的优势,”他说。这导致了 地标纸 去年发表于 手机 它布置了整个神经回路以实现愉快的触摸。
阿卜杜勒-萨布尔还开创了 疼痛的新定量测量 在老鼠身上,他和他的团队采用了一种工具来收集阿片类药物成瘾跨代遗传的证据。他在啮齿类动物中的研究结果表明,父母过度使用阿片类药物可能会改变基因表达,从而使儿童面临同样的风险。
阿卜杜斯-萨布尔因其成就获得了无数奖项,并被任命为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首届新生 弗里曼·赫博夫斯基学者 去年五月。该奖项在十年内向实验室促进多样性和包容性的新兴研究人员提供高达 8.6 万美元的资助。
广达 与阿卜杜斯-萨布尔谈论了他在科学领域重新开始的爱好、他的斑马鱼灵光一现以及他对新引进的裸鼹鼠群体的希望。为了清晰起见,采访内容已经过精简和编辑。
介绍
当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你的父母支持你对科学的兴趣吗?
他们确实做到了。我会开始买动物作为生日礼物,因为它们看到我对它们有多么着迷。快进到高中。九年级时,我的父母允许我在我们家的三楼进行为期一年的科学博览会项目,我正在为荣誉生物学做这个项目。我到处都有数百只小龙虾。我的父母不是科学家,但他们非常支持我在科学领域的冒险和冒险。
你的父母是做什么的?
我的母亲是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的首席财务官。我父亲退休前是一名精算师。所以我可能继承了数学天赋。为了近似动物的疼痛,我们进行统计建模,将其行为特征浓缩成一个易于阅读的量表。我父亲来听我的一些演讲,虽然生物学常常让他无法理解,但他对我工作中的数学部分感到非常兴奋。
大学如何塑造你的职业生涯?
我就读于一所历史悠久的黑人大学,北卡罗来纳 A&T。我的家族就读过这类大学。我的父母就读于霍华德大学。我姨妈也是。我的叔叔就读于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我的祖父就读于林肯大学。我不知道我是否有选择只能去这些大学之一。
尽管如此,我认为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看到与我相似的人确实做得很好,这增加了我的自信心。大学的文化是培育性的,而不是竞争性的。教职员工关心你。学生们一起努力并希望看到彼此成功。
介绍
你在大学做过研究吗?
是的。我知道研究经验很重要,所以在校园的第一个月,我挨家挨户向老师询问研究机会。我被雇到一家养猪场工作。这很有趣,因为我不吃猪肉,但我正在研究猪饮食的变化是否会改变肉的味道。
当时,我萌生了成为一名兽医的想法。所以在大二的时候,我在兽医医院工作,给动物做绝育、绝育和清洁工作。就在那时,我意识到我小时候对科学感到的兴奋不存在了。我并不喜欢那份工作。
但在大三和大四之间,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工作,一个灯泡突然亮了。我想,“哇,人们得到报酬是为了思考伟大的想法并试图找到对人类健康重要的问题的解决方案。”我记得我对父母说:“就是这样了。我想获得博士学位。在分子生物学中。”
是什么促使你研究快乐和痛苦?
这是一条有点蜿蜒的路。我获得了博士学位。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蛔虫中参与细胞发育的分子途径。至少 30% 的人类癌症中,该通路中的蛋白质基因发生突变。我的工作展示了这些途径如何控制细胞的基本类型和形状。我是该实验室第一个研究该途径的人,因此我必须从头开始构建很多工具。这是我整个职业生涯的一个主题:我喜欢制定新课程。
你规划的下一个课程将你带入神经科学。为什么?
神经科学似乎正处于其黄金时代。来自不同学科的人们聚集在一起研究大脑,但似乎问题仍然多于答案,所以我有发挥影响力的空间。我进入感觉神经科学的部分原因是它的逻辑简单:皮肤中的感受器被激活,然后在一系列中继之后你以某种方式在大脑中获得感知。在感觉系统中,触觉是研究最少的。一些重大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你是如何弥补自己知识匮乏的?
起初,我对自己缺乏正规培训感到不安全。作为一名博士后,我从未上过神经科学课程。在与神经科学家的会议和对话中,我经常发现自己跟不上。我不懂行话。但我一直定期与 迈克尔·努斯鲍姆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医学研究主任,在请他指导我之后。有一天,在他的办公室里,他建议给我辅导神经科学。从 1970 世纪 1980 年代和 XNUMX 年代开始,我们每周花两个小时讨论神经科学论文,持续了一年多。我就是这样学习神经科学的。这让我有勇气说:“好吧,我是一名神经科学家。”
我是非裔美国人。米奇·努斯鲍姆是一位来自纽约市的白人犹太男子。有时,生活中最支持您的人可能与您和您的文化没有任何直接联系。
介绍
您是如何制定疼痛量表的?
为了工作的痛苦,我退了一步。如果我们要使用小鼠来研究疼痛并可能开发新的止痛药,我们首先需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如何知道动物正在经历疼痛?传统上,研究人员会观察动物在刺激下收回爪子的频率,但动物移动爪子的原因有很多。由于没有标准化,不同的实验室会根据实验的不同来决定相同的刺激是无害的、痛苦的还是非常痛苦的。所以我说,“我们需要开发一个全新的系统。”
你是怎么想到这个主意的?
我的想法来自 迈克尔·格拉纳托,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位神经科学家,他的实验室离我们很近。他正在研究斑马鱼幼虫的声音惊吓反应。我参加了一个实验室会议,其中 罗山·贾因当时是格拉纳托实验室的博士后,现在是哈弗福德学院的教员,他谈到了如何使用高速摄像来捕捉速度太快而无法用肉眼观察的反应动作。我意识到我们可以使用相同的方法来记录动物响应皮肤刺激的动作,并使用这些动作来近似动物的疼痛。那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如果我没有去参加那次与斑马鱼科学家的会议,我永远不会有这个想法。我仍然去参加演讲,听人们谈论蠕虫、苍蝇、鱼、酵母、细菌——凡是你能想到的——因为也许我会学到一些可以融入到我们所做的工作中的东西。现代科学的耻辱在于,每个人都过度关注他们的系统、他们的方法、他们的有机体、他们的学科。当人们没有接受广泛的培训并且不走出自己的舒适区时,它可能会扼杀创新。
您如何将小鼠的运动与其体验联系起来以创建测量疼痛的量表?
首先,我们验证了一种被认为无害的刺激,比如触摸柔软的化妆刷,会激活动物皮肤中的触觉神经元,而针刺皮肤会激活疼痛神经元。然后我们记录了动物对每个刺激的反应动作。由于疼痛,动物会做鬼脸,迅速缩回爪子并用力摇晃。我们为每种类型的运动、缩回速度和爪子抖动次数给出了数值。然后,我们根据特征对疼痛水平的重要程度,为每个数字赋予一个数字权重,即特征值,然后将加权值组合成单个疼痛定量指标。
介绍
您如何看待这个新工具的使用?
有两件事让我们非常兴奋。其中之一正在研究遗传变异作为疼痛的驱动因素。全球人口对疼痛的敏感性差异很大。其中一些是社会文化的,但另一些则存在于 DNA 中。例如,感觉不到任何疼痛的人具有导致该特征的基因突变。在我的实验室中,我们使用疼痛量表来测量大约 20 种不同品系小鼠的疼痛敏感性。我们已经发现一些小鼠对疼痛反应不大,而另一些小鼠则非常敏感。我们正在使用基因图谱方法来寻找可能导致这种疼痛敏感性的新基因。
我们也对大脑如何控制从急性疼痛到慢性疼痛的转变感到非常兴奋。我们使用疼痛量表来测量小鼠的疼痛程度,然后使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拍摄小鼠大脑活动的快照。我们每天对动物进行成像,以寻找从急性疼痛转变为慢性疼痛的大脑活动模式。一旦我们找到它们,我们就可以尝试改变它们以改变慢性疼痛的进程。我们对这种疼痛的情感和感官成分感兴趣。
你研究过不痛的触摸吗?
是的,在我们最近 手机 在论文中,我们从皮肤到大脑来解释为什么某些形式的触摸是有益的。
这是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真是太神奇了。
触觉的分子研究仍处于相对初级阶段。不同类别触觉神经元的分子特征直到 2000 年代末才被识别。从那时起,很多注意力都集中在辨别性触摸上,这种触摸用于根据纹理区分 XNUMX 美分硬币和 XNUMX 毛钱。社交抚摸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这个项目是如何开始的?
大卫 - 安德森加州理工学院的研究小组于 2013 年报告称,皮肤中的某些细胞会对轻柔的触摸产生反应。但他们并没有将这些细胞与任何自然行为联系起来,也没有与大脑建立联系。我读了这篇论文并决定尝试填补这些空白。在我作为博士后的最后一年,我对小鼠进行了基因改造,使其具有对蓝光做出反应的温和触觉神经元。我的计划是用蓝光刺激神经元,看看老鼠做了什么。
当我在 2018 年开始自己的实验室时,我们已经准备好开始这些实验。我仍然记得学生们来到我的办公室向我展示他们的发现的那天。这就像灵光一现的时刻。当我们通过小鼠背部皮肤激活神经元时,这些动物的行为就好像它们在那里被抚摸一样。这启动了整个项目。我们做了更多的行为测试,并追踪了社交接触从皮肤到脊髓再到大脑奖励中心的路径。
介绍
发现这种皮肤到大脑的通路有什么医学意义吗?
是的,皮肤是一个很好的治疗目标。它很容易接近,并为大脑中让我们感觉良好的部分提供了一条直接的高速公路。如果我们可以用护肤霜打开这些神经元来改善心理健康——比如抵消社会孤立造成的伤害或治疗焦虑或抑郁,结果会怎样呢?当我在十二月就此发表演讲时,听众中的精神病学家和神经药理学家对其治疗潜力非常热情。
你有一群裸鼹鼠。你和他们一起做什么?
裸鼹鼠来自东非。它们生活在地下,基本上是盲人,严重依赖触觉,用胡须状的毛发在洞穴中导航并相互互动。触摸所占据的大脑区域是其他哺乳动物的三倍。我们相信触摸对于塑造他们的社区社会结构非常重要。
我们对它们感兴趣还因为鼹鼠感觉不到某种形式的疼痛。例如,它们对辣椒素分子没有疼痛反应,辣椒素是辣椒中的活性成分,而辣椒素对大多数哺乳动物来说是相当痛苦的。它们的皮肤上有对辣椒素有反应的受体,所以我推测这些动物的大脑通路可以消除疼痛。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并利用这些信号,我们可能会找到一种阻止疼痛的新方法。
作为一名年轻的研究人员,您必须克服哪些障碍,无论是科学的、社会的还是文化的?
总的来说,我很幸运能够拥有所有种族、国籍和性别的导师和同事,他们相信我并支持我。我比其他一些在充满挑战的环境中工作的少数族裔要幸运,正因为如此,他们今天不在这里。
也就是说,我并没有毫发无伤。大学警察拦住我并骚扰我,因为他们认为我不属于校园。我在自己的大楼里被拦住,当局已传唤我。我认识的大多数其他黑人科学家都有过非常相似的经历。这些事情不仅发生在大学里,也发生在我居住的社区,当它们发生时,他们会感觉不舒服,并会激起愤怒和沮丧。但我一直有一个支持我的人网络,他们帮助我度过了职业生涯中相对较少的几次经历这种公开种族主义的时期。
您对有抱负的黑人科学家有什么建议吗?
天空才是极限。如果环顾四周并没有看到很多与你相似的人,请不要感到痛苦,因为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让自己周围都是优秀的人。有时这些人看起来很像您,但如果您的一些最大支持者与您不同,请不要感到惊讶。保持开放并建立正确的联系。
并且不要粉碎自己的梦想。我们需要来自各种背景、各行各业的人,因为我们面临着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我会鼓励黑人科学家或任何对这项工作感兴趣的人:如果你对它有热爱和热情,那就去做吧。